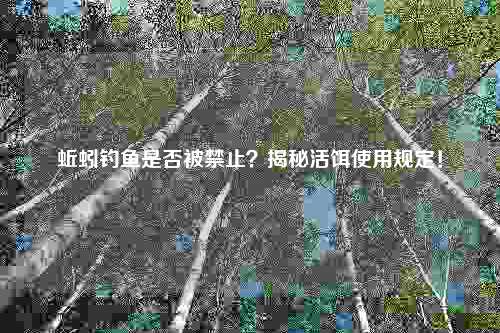吴俊范 |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
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主要分布在湖荡丰富的平原水乡地区,以池塘养鱼为主,外荡养鱼为补充。与粗放型的外荡养鱼相比,池塘养鱼业具有集约性强、产量高等特点,与日益发展的城市市场相适应。作为一种生态型农副业,池塘养鱼的饵料利用河湖的自然物产、农业生产废料和农产品加工的下脚料,使池塘物质与外界的循环通畅无阻。官河湖是野生鱼的渊薮,原不用于人工养鱼,但在商品经济和增产观念的刺激下,也逐渐成为养鱼公司扩张的场地,传统水利格局面临着重大改变。官河湖养鱼导致的大型水体排蓄效能失序和水质下降等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求水面高产的浪潮中进一步加重。
太湖流域河湖面积广大,依托于自然河湖的淡水鱼捕捞业长期在区域经济和民众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中叶以来,该区淡水鱼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人工养鱼业以绝对优势超过自然捕捞业,并将大面积的河湖自然水面变为人工养鱼场。以位于湖荡水网地区的青浦县为例,1955年全县用来养鱼的水面仅有0.12万亩,1956年达到1.5万亩,1957年即达3万亩 ;经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养鱼水面增长更快,到1982年已增至13万亩,占境内全部地表水面积的76%,半数以上的养鱼水面属于江河湖泊自然水体。人工养鱼业向自然水体的直线式扩张,带来一系列水环境问题,如水体分割造成河湖排蓄能力下降、调剂旱涝的能力减小,过度投饵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环境变化乃积渐所至,20世纪中叶以来太湖流域自然水面利用方式的转变和相关水环境问题不可能骤然发生,那么在此之前,该地区的淡水鱼生产方式以及河湖水面的利用机制究竟如何?河湖水环境的变化在历史脉络上有何关联?本文即从生态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相结合的角度,详细复原民国时期的人工养鱼业以及河湖水资源的利用机制,以进一步厘清近半个世纪中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人地关系机制。

民国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是西风东渐的先锋地区,人们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观念、方式和力度相应发生变化,那么,淡水渔业作为一种以河湖之水为直接生产资料的传统农副业,其在保持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发生了哪些现代性变革?河湖水环境效应如何?相关研究论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比较简略。如王建革在考察1800年至1960年间松江县华阳桥的水、肥、土生态时,将1950年作为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分界点,并把民国时期的情况包含在传统范畴内,对民国地方性水土利用观念等方面新旧交替的特征未作专门论述。李玉尚、顾维方专门研究了16世纪之后绍兴地区的河道养鱼,对民国时期绍兴养鱼业向本地和周边湖荡扩展的事实有所论及,但重点并不在民国养鱼生态转型上。高梁对明清以来池塘养鱼基础深厚的菱湖、洞庭山等地多有描述,但也未涉及民国时期池塘、外荡渔业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上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一批江浙沪地区渔业史志,亦主要是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渔业生产情况,对于民国时期的状况言之寥寥。
本文运用江浙沪等地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渔政管理和养鱼纠纷方面的档案与民国期刊,力求复原民国时期太湖流域人工养鱼的业态分布和水环境状况,以及政府和民众在水资源利用上的观念和态度。在此基础上,试图在工业化这一时代背景下对20世纪以来太湖流域淡水渔业的转型机制作出思考。
明清以降,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池塘养鱼作为一种适应水乡地理环境的农村副业得到长足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浙西杭湖一带的农民对于池塘养鱼已“泰半兼营之” ,苏南水乡农民也“大多以饲养内河鱼鲜为终身副业” ,这说明池塘养鱼在当时太湖平原水网地带已呈普遍发展之势。
李伯重在论及明清江南农民利用水资源方面的优厚条件时,认为养鱼是其主要表现之一,因养鱼本轻利重,时人把养鱼列为畜牧养殖业之首(相对于饲养猪、羊、鸡、鹅、鸭而言) ,但对其在当时江南农业生态链条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及相关人地关系并无详细考述。基于民国史料相对丰富,本文尝试从养鱼区的空间分布、资源利用与循环、鱼塘商品化与鱼产品的市场环境等几个方面,展现当时最主要的人工养鱼形态——池塘养鱼业的经济与生态图景,并参考相关经济数据对鱼塘的产量和效益作出大致评估。
池塘养鱼,即把从河川湖沼中捕取的鱼卵孵化为鱼苗后,放入筑有堤坝或挖深的池塘中加以人工饲养,是一种水土结合式的养鱼方法。据民国文献中所载,按照池塘养鱼的水源和鱼塘集中区的地理环境差异,可将太湖流域的池塘养鱼分为两种类型:平原水乡地区的池塘养鱼和环湖泊地区的池塘养鱼。前者主要指苏南、浙西多水荡的低洼平原,后者则主要利用各大湖泊周围丰富的滩地和沼泽。
平原水乡型的池塘养鱼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太仓、昆山平原水网地区,与明清时人所认知的“江南腹心”地带基本重合。开塘养鱼能够为农家带来较高收益,又兼有改良低洼地的功用,所以在低洼多湖荡的水乡农村具有开塘养鱼的传统。清初桐乡人张履祥所著《补农书》,在《策邬氏生业》一篇中对其友人邬氏的小农场进行了综合规划,建议邬家将一方池塘专门蓄鱼,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养鱼的塘泥不仅可以为桑地提供肥料,且年终售鱼的收入“每亩可养二三人”,比种植豆麦、竹子、果树的收益都要高。此例从侧面说明,在17世纪的江南水乡,池塘养鱼已成为农家商品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副业的优先考虑对象。
近代以来,随着江南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量不宜种粮种桑的低洼地,以及河湖岸线新淤涨的滩地,继续被开发为鱼塘。1925年官方编写的《太湖流域农田水利略》,明确鼓励农民根据水土条件,将下洼地改造为鱼塘以增加经济收益:“不能栽培稻作之中等田,应就各地方土质、气候、市场需要,种植兰、蒲、茭、荷、菱、芡等水生植物,若最下之釜底,不能栽培水生植物,则建筑鱼塘,培养鱼鳖虾蟹蛤蜊,增加水产收入,使上田下田均得增进植产。”
1932年江苏省建设厅专门对地势低洼县份的池塘养鱼潜力做了一次调查,目的在于发掘尚未充分利用的官荒地,鼓励个人或公司通过租赁或购买,建成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鱼塘。《渔况》杂志第49期公布了此次调查的官荒数据:
表1中统计的主要是新增加的官有湖滩、洼地和荒荡,官方鼓励民间领租养鱼,其前提是认为这种土地利用方式适合本区地理环境,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正如调查报告开头所说:“苏省各县荒地颇多,内中之洼地可开辟为池,以养殖鱼类者,亦复不少,且开池之泥,可以填高他处,变为良田,两得其利。” 此处统计仅为最近生成而尚未利用的荡洼地,若将时段放长来看,此类被开垦成鱼池的土地数量相当可观。再者,民间自主开辟的大量鱼池并未包含在这次统计范围内。
环湖泊型的池塘养鱼,顾名思义,就是环绕湖泊岸线的滩地而分布,在空间上比水网地区利用洼地随机开造的鱼塘更具集聚性。此以太湖东南岸以及阳澄湖、淀山湖等大中型湖泊周围最为典型。
环湖泊鱼塘能够直接利用天然湖水和湖泊物产作为养鱼资源,这是较之低洼地鱼塘的另一优势。养鱼用水直接引自湖泊,水中微生物也随之流入池塘,丰富的微生物可作为鱼类饵料,就近从湖中捕捞螺蛳、蚬子等也比较便利。太湖北岸无锡的鱼塘,主要分布在太湖两大出水口仙蠡墩和大渲口附近,直接“用太湖之水,由梁溪导入,水量甚丰,水色亦清,水中含有丰富之酸素有机物及微量之盐化物”。这一带的鱼塘总数,在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复原期仍保持有3000多个,每年养殖鱼的产量尚有数万担之多 ,由此可推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期此处池塘养殖业的盛况。苏州也是利用太湖水养鱼的典型,养鱼塘集中分布在阊门、齐门以外的近郊区。此处不仅邻接太湖,用水便利,且养殖的鱼产品可就近销往苏州市区,运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水路航运也颇为便捷。据1946年调查,苏州城外的养鱼池“总数有四千以上,池之面积大抵为二三亩至二十亩左右,从事养殖之鱼户约有千余户,每年生产额约十万余担左右”。
民国时期,养鱼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本轻利重的产业,各种宣传养鱼的文章频见报端。这类宣传当然是把正在扩大中的河湖自然水面养鱼包括在内,粗放的用水方式确实成本低廉。而已经得到稳固发展的池塘养鱼业,在时人看来也具有成本小、获利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养鱼饵料的丰富性和供给便利,以及池塘剩余物质的可再利用性和循环通畅。池塘养鱼的饵料,基本是利用本地河湖的自然物产、农业生产废料和农产品加工的下脚料,不需要远距离运输,池塘剩余物质与外界物质可以转换和互补。
平原水网地区水流缓慢,河湖水体中富含鱼类生长所需的各种天然食料,养鱼户无论自己采集鱼饵,还是购买商品性鱼饵,均甚为方便。无锡养鱼户所用之饵料,一般采取水草、旱草、蚬子、螺蛳等自然食料与大麦、豆饼等人工食料搭配的办法,“青草随地可割取,螺蛳购自宜兴、太湖、常州等处,蚬子或螺蛳一元皆可购回二十五桶,每桶容二斗五升”。养鱼户除了自己就近从河浜湖荡中采捕萍草、螺蛳等水中物产,不敷的部分则从市镇上的鱼行、饵料行、杂粮店、榨油坊等处购买。供应鱼饵的店铺不仅大量供应豆饼、大麦、菜饼等农副产品之类的饵料,也收买乡人农闲时从附近河荡中采集的螺蛳、蚬子等水产,再转手卖给养鱼户。池塘养鱼集中的地方对于商品性饵料的需求也大,于是镇上的饵料商行比较密集,20世纪30年代仅菱湖镇上就有百余家饵料行。
除自然饵料和农产品加工的下脚料外,农桑生产的废料,如羊粪、蚕沙等,也可用来养鱼;一种鱼类的排泄物亦可成为另一种鱼类的食物,如草鱼的粪便为鲢鱼所喜食,因此鲢草混养比较常见。这些方法使得废弃物进入新一轮生态循环,属于江南生态农业的一部分。
由于鱼塘用水和饵料基本取自本地生态环境,甚少有外源性的能量投入,养鱼产生的塘泥和废水也能够被周围环境所消解,很少产生多余的污染物。根据近来菱湖养鱼老农的回忆,早先当地的塘泥和湖泥肥力都很高,富含鱼类排泄物和鱼饵食料残渣等营养物质,最适合桑园施肥。民国时期该地的桑园很少使用化肥,所用的主要肥料就是鱼塘中的塘泥。菱湖鱼塘多,出产的塘泥足够种桑使用。通过挖出塘泥,也起到定期清除鱼塘里剩余营养物质残留的作用,对净化水质有好处。至于鱼塘换水,以前菱湖农民每隔2—5年就要更换一次水,因塘泥经常清理,这种塘水肥力不高,排入外河湖也不会污染水体。
水乡地区的鱼塘与稻田一样,具有完善的产权,小农可根据生产需要和人力进行买卖和转让。这说明经过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鱼塘已成为这些地区土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养鱼户可以自养谋利,也可以出租给他人经营,很少因产权不清而产生纠纷。1929年无锡地方政府对太湖之滨养鱼村的调查发现,村中鱼池大部分属于私产,由农户自家经营,也有的属于家族共有财产,如祠堂池、杨河池等。村民中也有利用公共池塘养鱼者,需要与族里履行租赁手续,之前从未引起过产权纷争。
民国时水乡地区鱼塘的买卖和租赁价格与种植粮食作物的粮田耕地基本持平,这说明鱼塘经济效益较高。一方面,水乡养鱼本轻利厚;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对蛋白质食物的需求以及口岸城市贸易的增长也起了促进作用。池塘养鱼的集中化在民国时有所发展,也带动鱼塘交易价格进一步提升。1932年对东太湖洞庭山一带的调查显示,“鱼池自营者颇鲜,大都出租他人”,经营鱼塘的专业户较多,鱼池的租价为每亩4元。1939年时吴兴县东北部的连片鱼荡多出租给擅长养鱼的绍兴人经营,每亩鱼荡的租金为10元左右。当年吴兴县鱼荡地买卖的价格为每亩60元,稻田买卖的价格为每亩50元—80元。而根据1940年满铁调查资料,南通县头总庙村的平均地价为每亩75元 ,可见该时期苏南地区的耕地价格差异不大,而鱼池的交易价格与耕地价格基本持平。1920年代对无锡养鱼区的调查也显示,鱼塘的租金和买卖价格都比较高,租赁鱼池1亩须洋6元,购鱼池1亩则须洋百元以上。上述几个调查的时间和地点虽不同,但反映出鱼池价格水平在土地交易序列中的地位比较稳定,与稻田一样,也在土地市场上频繁交易。
随着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方式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民国时期养鱼户生产的鱼产品与各级城市市场的对接更加便捷,需求量增加,进一步推动了池塘养鱼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大城市对鱼货的需求最大,除了城市居民消费,还有部分转口和出口,沿铁路和轮船航线年上海鱼市场对河鲜鱼销量和去向的统计显示,该年份输入上海市的河鲜鱼数量为19.6万担,其中沿沪杭线万多担,沿京沪线万多担。
河鲜鱼的主要消费市场还包括无锡、昆山、常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基层市镇的消费也占一定比重。但是各地鱼货销往周边城市的比例根据地缘关系有所不同。据1948年浙江省建设厅对部分产鱼区鱼产品去向的统计(包括捕捞鱼和养殖鱼):嘉善县主要产野生鱼,年产0.8万余担,其中半数销往上海和杭州;杭县以野生鱼为主,年产1万余担,销往杭州的占四成,二成销往上海;萧山县池塘养鱼业发达,年产11万余担,销售地为上海、杭州和江西省一些城市;绍兴主要产外荡鱼,比池塘养鱼区的产量少,年约3万担,就近供应宁波;吴兴县是池塘养鱼集中区,年产30万担,销售市场除了沪、苏、杭等大城市之外,也就近供应中等城市无锡和昆山。
上述统计未将野生鱼的主要产地,即大中型湖泊地区的产量包含在内,因此不能完全据此评估养殖鱼与野生鱼产量之高下。由此可见,池塘养殖鱼在长三角地区淡水鱼产和市场供应量方面均已占据重要份额。在一些集约化的养鱼区,如上述萧山与吴兴地区,人工养鱼产量绝对超过野生鱼产量。
1934年上海鱼市场河鲜鱼行公布的资料,也说明了池塘养殖鱼已占城市鱼市场的半壁江山:“上海市一方为海产鱼介之大集散地,一方亦为河鲜鱼类之重要销售市场。而河鲜鱼类之来源,概分两种。一为长江沿岸各埠运来之河鲜鱼,此以在内地河川中捕获运来销售者,其种类以鲥鱼、刀鱼、鲫鱼、鲤鱼等为多数;一为江浙之嘉兴、菱湖、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运来之养殖鱼,此为当地民间开辟池塘养殖成长后运来销售者,其种类以青鱼、草鱼、鲢鱼、鳊鱼、鲤鱼等为多数。每年二项河鲜鱼在上海之销售数字,亦达三十万担(系多年平均数字的估算),价值四百万元左右。” 此报告似乎只强调长江沿岸各埠所产的野生鱼,而对太湖流域各大湖泊所产的野生鱼有所忽略。不过据此报告可知,民国时期太湖流域水乡地带池塘养鱼的优势普遍得到了发展。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池塘养鱼在江南水乡地区广泛分布,地势低洼、湖荡连片的地带则形成规模较大的集中养鱼区(如上述菱湖)。在当地农业经济中,养鱼业甚至超过种植业和桑蚕业的地位。对农民而言,养鱼是为增加收入,那么从事池塘养鱼的收益究竟如何?以下根据相关资料对典型地区的鱼塘产量和农民收益情况做一个大致估算。
1923年渔政管理人员张伯铭对苏南养鱼区无锡的鱼塘产量和收益进行调查,该报告云:“五亩之池一年可出青鱼三十担,草鱼约三担乃至五担,鲢鱼二十余担,鳊鱼十余担,鲤鱼二十余担。大鱼多销于江阴、宜兴、常熟、无锡等处。至大鱼之价格,青鱼一担约售二十五元,草鱼及鳊鱼约售十七八元,鲢鱼及鲤鱼约售十一二元。” 根据这份报告,一方5亩的鱼池一年至少可出鱼80担,平均亩产达16担,即1600斤。为了判定这个亩产量在当时苏南地区处于何种水平,可将其与后来的年代以及同时期周边地区的产量做一对比,甚至也可与外荡粗养方式的鱼产量进行对比。
据1950年代浙江省农业厅档案,1955年该省池塘养鱼平均亩产量是143斤,最高的是1084斤,最低的只有30余斤;而外荡养鱼平均亩产量为64斤,最高的是220斤左右,最低的只有20余斤。对比可知,1920年代像无锡这种典型养鱼区的池塘精养鱼产量是相当高的,比1950年代浙江省池塘养鱼的最高亩产量还要高出若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跃进式地扩展养鱼面积(包括扩大池塘面积和国营鱼场经营的外荡、河湖面积),产量反而下降不少,且参差不齐,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与外荡粗养的产鱼量相比,池塘养鱼的优势也相当突出,上引1950年代的档案资料已可初步说明。另外,还可与民国时期外荡养鱼最为典型的绍兴地区的鱼产量作进一步比照。绍兴北部平原地区湖荡密布,其水土环境和经济结构与杭嘉湖平原颇具一体性,外荡养鱼久负盛名。根据1946年《申报》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绍兴全县鱼荡的面积在10万亩以上,在抗战前,年产可达500万斤—600万斤。据此推测,抗战前绍兴荡鱼的平均亩产约为50斤。当时外荡养鱼属于一种粗放管理、完全利用天然饵料的养鱼方式,其亩产量大大低于精养鱼塘。
以下再对浙西水乡典型养鱼区嘉兴的池塘产量和农民收益做些评估,并结合无锡的情况进行讨论。1940年浙江省政府农矿部对嘉兴县养鱼池的一份专项调查显示:全县养鱼池总面积为1万亩左右,最小者1亩,最大者3亩,最大鱼池年约产鱼五六十担,最小者约20担左右。据此推算,每亩养鱼池年产鱼平均为20担,合2000斤,比上述苏南无锡1920年代的产量略高。
就农民收益而言,以1940年嘉兴养殖鱼的售价乘以产量计算一下,再减去农民投入的鱼苗钱、饲料钱、鱼池租金及人力等,另外加上鱼塘堤岸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估计每亩鱼塘的纯收入在100元上下。而1923年对无锡养鱼区的调查则明确指出,有一户吴姓农民的鱼池每亩年收入为80余元,在村中属一般水平,相比于上述嘉兴鱼塘之亩收入稍低。1938—1939年满铁曾对苏南6县12村农户年收入构成进行调查,户均年收入为228元(包括种植业和桑蚕、竹编、畜牧业等收入合计)。将苏南地区农户年均总收入水平与养鱼收入对比可以看到,假设养鱼户的池塘面积达到2亩—3亩,其养鱼所得收益即相当于非养鱼户各种产业相加的收益。所以从实际经济效益来看,低乡湖荡地区发展池塘养鱼实可为农民致富之道。
通过以上对太湖流域池塘养鱼业各要素的分析,可见池塘养鱼发达的低乡一带,同时也是历史悠久的圩田农业区和商品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地势低洼的水乡平原,圩田模式下的稻、桑、鱼三产业相互促进,通过广泛开挖池塘营造了高低错落的地形,使水有所归、粮有所种、鱼有所养,是为一种充分利用水乡地理环境的生态农业。李伯重曾指出明代中期以来江南农业发展的两条主要途径,即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通过不断提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水平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来发展生产 ,这两点在民国时期江南水乡地区池塘养鱼业的开发中均得到生动体现。农民将低产的洼地改造为高产的鱼塘,或将湖滩沼泽地加以改造,首先是更合理地利用了水土资源,提高了生产率;同时,投入人工和各种资源成本养鱼,主要是为了上市出售,增加家庭收入,也迎合了城市市场和工业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较高的商品价值。其次是养鱼的饵料也可在区域水环境和农业生产环境框架内解决,而基本不需要外源性投入。因此,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池塘养鱼业是一种经济效益高、生态链条通顺的产业。
外荡养鱼亦是江南水乡淡水鱼生产的主要方式,与池塘养鱼一样具有悠久历史。“外荡”与池塘养鱼的“内塘”相对,特指水面较大、没有封闭性堤岸圈围的自然河流或湖荡。民国农学家何西亚在浙西养鱼事业的报告中说:“养鱼有池鱼与荡鱼之别。池者,即户前屋后陇亩道旁之池沼也,养鱼其中,俗名鱼池;鱼荡者,即于外河中用竹帘截签若干距离面积之水面而成,养鱼其中,俗名外荡鱼。” 因大型湖荡或水漾兼有多种水利功能,如种菱、积肥、通航、灌溉、蓄排等,受益群体众多,故制约外荡养鱼发展的因素比较复杂。
外荡养鱼的特点是“粗养”,投入成本比池塘养鱼少得多,主要是簾簖、鱼苗和少许看顾的人力。这看起来似乎是外荡养鱼的成本优势,但就产量保障而言则成为弱势。首先,荡主需建造竹质的簾簖,将水体平稳的水荡与流动的外河相隔,或将自家所有的荡面与邻家水面隔开区界,以防止逃鱼。竹篾柔软有弹性,不致于影响船只通行。只有在不通舟楫的水荡与河流的接口处,才会筑起土坝,以避免鱼类外溢,这通常是在大河的港汊或水荡的湾角。其次,须投入一定数量的鱼苗成本,一般为鲢、鳙、青、草等池塘里惯常养殖的、成长较快的家鱼类。江南本地河湖并不产出此类鱼苗,鱼苗贩户每年春季从长江中游捕捞鱼花的人手中收购,长途贩运至江南,再出售给养鱼户。再次,外荡养鱼需专人看管,要投入一定的人力成本。外荡面积广大,向村庄远处延伸,荡鱼常面临被盗或强抢的情况。总之,相对于池塘精养需要开挖和维护池塘、筑造堤岸、投入大量饵料、每日精心饲养,外荡养鱼节约成本的特点十分突出,但其产量和收获的稳定性却远远低于前者。
制约外荡养鱼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自然饵料获取与公共水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外荡养鱼完全依靠水体中自然滋生的物质,如螺蛳、水草、各种微生物等,农民向荡中投放哪种鱼苗,如何将不同种类的鱼苗搭配成合适的比例,不仅需要对水质和水中营养成分了如指掌,还须考虑所利用水面的公共水资源性质,顾及水面的其他用途,如蓄排水、种植菱藕等水生物、交通行船等,否则就会因饵料不足或纠纷不断影响收成。饵料问题与争夺水资源的纠纷时常纠缠在一起,制约着外荡养鱼的产量增长和面积扩张。下面以饵料来源最广的草鱼养殖为例,对公共水资源利用中的矛盾予以具体说明。
草鱼以岸草和萍草为食,这种草食所在皆有,故草鱼颇得外荡养鱼者青睐。但在大荡中饲养草鱼不能只图个人私利,要同时兼顾其他农户的利益。大荡通常是综合利用的,荡面权和荡底权分开,各有其主,荡面种菱,荡底养鱼,各自纳税完粮。荡主对于养鱼或种菱的选择,也常根据其经济实力和市场情况而变动。像杭州城河以及城郊的古荡、塘西、丁山湖等村庄的多数河浜,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其中养鱼,但许多农家有余钱买鱼苗就养鱼,无钱就种菱,所以河荡中通常都是鱼菱并存的格局。一大片水荡的使用权分属多家荡主,荡主又可将水面或水底权租赁给其他农户经营,这使得湖荡的用益权变得更加细微而复杂。
养鱼户与其他农户的许多纠纷,都是因养鱼户私养草鱼妨碍了其他人种菱和罱取湖泥引起。例如萧山县东蜀乡的历墅湖,面积广大,每一片各有完粮之人。20世纪30年代,水面仍由完粮人及傍湖菱户种菱,水底则租给曹阿元、周竹仙等多户村民养鱼。不料曹等未经商量私自在历墅湖放养草鱼,引起菱户周妙庭等控告到县府,告发的理由,是养草鱼不仅损害菱收,且“草鱼咬吃湖菱,秋后无败叶残枝下沉湖底,失去肥料价值,不能壅田,妨碍农业”,使得滨湖稻田缺少肥料。萧山县政府果断处理,判决历墅湖今后“绝对禁止放养草鱼”,必须农产和鱼产兼顾。
鱼—菱—肥式的纠纷(因养鱼、种菱与积肥之间的矛盾而引起)在水乡湖荡地区较为普遍,除官方应对处理外,民间也相应形成了自我约束、相互监督的机制。吴兴县菱湖以池塘养鱼闻名江南,且外荡养鱼也有悠久传统,“该处湖面甚多,如天化漾、横山漾、方溪漾、小溪漾、清水漾、卞家漾等不下三四十,其面积大者一二百亩,小者数十亩,多属公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地人多将水荡租给擅长养鱼的绍兴人经营,但对于草鱼的养殖专门设定了严格约规:“所养鱼类,以花白鲢为大宗,青鱼、鳊鱼、鲤鱼亦养之,惟草鱼放养,则为本地人所不许,因其地河面皆种菱,倘若养草鱼,则湖内之菱将为所食,损失甚大,故公河以内,取缔草鱼之养殖。”
山阴县鉴湖也发生过农户联合抵制养草鱼的事情。鉴湖周围的乡民多年来已形成习惯,不在湖中养草鱼,以杜绝草鱼咬伤菱花之发生。但1905年忽有鱼户魏大贞私养草鱼,即刻遭到乡民联合投诉,最终官府要求魏大贞将尚未养成的草鱼速行捕取出湖,立即终止饲养草鱼。
由此看来,作为人工养殖优势鱼种的草鱼,实际上更适合池养,其以草为食、节约饵料的优点在池塘精养中可得到充分发挥,但在自然水面中养殖,则受到食物链以及渔农共享生态的制约。
由于前述种种制约,外荡养鱼产量不高。20世纪30年代萧山地区外荡养鱼的亩产在50斤左右,租荡户还要向荡主纳鱼5—20斤作为荡租,所剩有限。而与杭嘉湖平原毗邻的绍兴水网地区在1940年代的亩产量也大致只有50斤。本文第一部分对池塘单产有过估算,二者相比,可知外荡养鱼的亩产量仅相当于池养亩产量的1/15至1/20。
再就某一区域的总产量进行估算,外荡养鱼同池塘养鱼的差距也很大。嘉兴北部的农民向有在湖沼河浜中设簖取鱼的习惯,每年清明前后放秧,冬至收获,据1948年的统计数字,这一区片每年总产量只有大约2000担 ,而嘉兴全县鱼塘的总产量每年却达到20万担。再与主要倚重池塘养鱼的吴县作对比,即使在抗战胜利后的经济恢复期,吴县池塘养鱼的年产量也达到30万担 ,外荡与池塘养殖的产量差距更为明显。
由于外荡养鱼产量小,其在供应市场消费方面只能作为池塘养鱼产品的补充。综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鱼市场的淡水鱼消费,养殖鱼供应量与江河湖泊捕捞的野生鱼量有比肩之势 ,但人工养殖的鱼产品主要是来自菱湖、嘉兴、吴县、洞庭山等水乡地带的池塘养鱼,而不是外荡养鱼。
虽然外荡养鱼产量有限,但农户占用外荡水面的面积却比较大。人们通过增加养殖面积规模来弥补单产低微的缺憾。萧山外荡养鱼向称发达,全县鱼荡约有80余处,养鱼户约有3000余家,鱼荡面积,大的约四五百亩,小的约三四十亩,百亩左右的荡,为数最多。由于鱼饵全靠水中天然所产,占用越大的水面就意味着拥有越丰富的饵料来源,向阔大的水体投入人工饵料显然是不可取的。正如1936年一份嘉湖地区的渔业调查报告所云:“养鱼以饲天然料为原则,若时时供给食料,则获利难矣。” 因此对天然饵料的谋求时时助长着乡民们扩张养鱼面积的欲望。
但江南水乡湖荡使用权的细微化和长期磨合而成的小范围的公共水利秩序,限制着外荡养鱼的扩张。在当时的农副业生产格局下,用于养鱼的水面总量或投放鱼苗的密度超过一定限度,自然会受到水生作物种植户和周围农民的抵制。过分分割水面对旱涝排蓄和交通也有影响。民国时期关于外荡的叙述文本中,常用“公有”二字 ,此所谓“公有”,与官方直接控制、不许民间私自使用的“官河湖”是有区别的(下文专门讨论),主要是指这些湖荡的自然物产和水资源为一定区域内的民众所共享,形成一个小范围各业共存的公共水利圈,圈中秩序主要靠受益者自觉地参与和维护,因为湖荡的使用权归属个体的民户。
由上可见,当时对于中小型公共水体的利用机制,官方强制性管理并不是主要的,民间存在基于利益共享的自我调控和相互监督。外荡养鱼户试图通过扩大水面来增产的欲求,在这种小范围的水利维护机制下难有作为。尽管外荡养鱼成本更小,市场对鱼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但扩张面积需要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和生态代价,只能作为池塘养鱼的补充形式而存在。
民国时期的江南地区深刻地卷入了“世界经济系统”,农业商品化快速发展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向作为公共水利资源而并不用于商品生产的“官河湖”,其利用观念是否也发生明显改变?商业性养鱼是否开始向官河湖扩张?
官河湖与民用的河湖荡在产权意义上有本质不同,学界对官河湖利用方式和管理体制的历史变化已有所讨论,其中产权与渔业生产的关系受到更多关注。归纳起来,官河湖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它是一个区域社会和民众所共享的“公共水利体”,即其具有向某一区域广大民众和社会提供通航运输、渔业、农田灌溉、排洪排涝、生活饮水等多方面的功能,故不可为某一团体、某一部门占为专用,不可过度用于某一产业的发展。官方对大型水体一向严加管理,以避免垄断、维持地方水利安全和民众生计的正常运转。历代地方志所载政府对大型河湖的疏浚治理、重要水利工程的实施以及禁止占垦河湖的措施,可充分说明官方对大型水体管理的重视。日本学者森田明对清代江南区域内杭州的西湖、余杭县的南湖和南京城的河湖水利管理与经费筹措体制进行了详细研究,其涉及的湖泊无论是在城还是在乡,官方的一致做法,均是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护湖泊的综合水利功能,从而保持地方社会和民众从中受惠。
具体到水网密布的江南水乡地区,河湖产权另有地理环境方面的特殊性。由于地势低平,水体连片,官河湖与民用的水荡、河浜等常常连为一体、界限不明,一大片水域的边缘部分、支汊和湾角可能为民用,中间的主河道或阔大湖面则为官有,因此在实际使用中更易引发纠纷。举例来说,1938年绍兴县袍渎乡政府因建立养鱼实验荡,将“私有荡产与公用水面毗连”的洋港荡占为公有,甲长俞阿图联合乡民向县府控告,即是因为大湖荡的公、私产权边界不明所导致。俞阿图等人坚持认为,“洋港荡本为民等数百家向来、种菱、捞泥,以为生活生产之荡,如果政府既热心事业,认以养鱼为有利益,应促进改良,不应将民等私有产权剥夺占为公有”。县政府承认洋港荡的产权复杂性,决定区别对待:凡系私产的完粮之荡,仍归百姓租赁养鱼;凡“可通运之河道”“天然形成之湖沼而为公共需用者”以及“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均不得占为私有,如已经占有者,应履行渔业登记,由政府重新审查其产权性质。该案反映出江南地区的大型水体有着公、私权限交织并存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判断河湖官有属性的标准,主要是考虑受益群体的范围是否广大,以及河湖水体的功能是否多元化,如服务于大范围内公共交通、蓄排、饮水等方面的功能。
江南地区民众对官河湖的利用权,在民国时期是相对开放的。张朝阳的研究指出,在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5—1686年)江南地区已经基本完成豁免官河湖渔税的进程,民众可免税在官河湖从事、挖泥、采草等作业。后来虽事实上仍存在豪强圈占和某些地方政府阶段性征收渔租的现象,但总体上官河湖的使用权面向社会。1935年一份对淀山湖利用情况的报告,反映了当时大型湖泊为周边民众生计所共同依赖的图景:“湖水澄清,烟波浩渺,湖中产鱼虾等水产动物极富,尤以秋蟹最著声誉。滨湖渔民,恃此湖为生者,不可胜数。湖底水草淤泥,可为农田肥料,湖畔农户,咸取给于是。每当春夏之交,四乡农民放船来湖夹取草泥者,络绎不绝,诚天然一富源也。” 需要强调的是,官河湖面向社会开放与中小型湖荡产权归属私人是截然不同的,官河湖具有斯考特·戈登(H.S.Gordon)所归纳的“公地资源”性质,既是属于所有人的财产,又不属于任何人专有,因此最容易被过度侵占而发生“公地的悲剧”。
20世纪初期,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刺激下,首先从政府观念的层面上开始了圈占官河湖水面进行养鱼的商业活动,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逐利性。
圈占官河湖养鱼,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背景的公共团体直接参与,例如以县渔会、高等院校、农业推广所、乡镇公所、地方慈善机关等名义,创办养鱼试验荡、养鱼农场等,这些官方机构在取得水面经营权方面享有公权力的优势;二是地方绅商借鉴西方企业经营模式,创办养鱼公司,以较大的资本投入和雇佣较多人力进行规模化的养鱼生产。这样的公司式经营在当时受到官方支持,甚至有官方机构出面与绅商联合开办养鱼公司。
圈占大水面势必对渔民生计和周边地区的农田水利与旱涝调节带来影响,产生各种水利矛盾。通过稽查民国档案中与养鱼相关的水利纠纷案例,可以得知,官方态度由最初的严格审批转向后来的习以为常,管理松懈,再到政府本身也直接参与,这表示商业性开发自然水资源的风气逐渐加强。
民国初期,地方政府已开始允许私人创办养鱼公司,但必须由官方查勘认定租荡筑簖对民众生计和农田水利确无妨碍的情况下方许开办。若公司开办后遭舆情反对,政府站在公共水利的立场上调解争端。1915年震泽严绍贤“为振兴实业起见”设立渔业公司,租赁大片河荡筑簖养鱼,但遭到士绅代表陆进法、张嘉桐等的投诉。其理由,一是渔业公司扼断了渔民入荡的权利,二是梅雨季节宣泄不畅,使周围的秧田积水并产量受损,总之是“以少数人之利益影响多数人”,故要求渔业公司立即终止经营,将鱼簖全部拔除。这表明圈占大水面垄断性养鱼,引起的水利与社会矛盾确实是多方面的,对此县政府也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和调解。
此时的公司式养鱼虽处于试验和探索阶段,但无论政府方还是公司方,对于大水面养鱼的经济收益均抱有信心,乐观地认为通过扩展水面即可获得规模化的收益。1910年南汇六灶镇区董张雏声发起创办渔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满怀希望地筹集了1.5万股资金,每股大洋2角,然后将一条公共河港筑簖围拦,投入鱼苗10万尾。当时集股人皆认为,经过三年后鱼苗长成出售,一定会以鱼类数量庞大而获得巨利。官方则通过把河湖大水面租赁给养鱼公司经营成为受益者,因为公司方需向政府缴纳为数不菲的水面使用费和保证金。对地方财政来说,这比起原来免费将官河湖向渔民等开放或者只收取少许税费,要增加不少收入。1916年南京八府塘渔户联合投诉孙鹪巢的养鱼公司侵夺了众人生计,就提到各渔户原先“虽缴官费,岁仅五六十元”,而“近有孙鹪巢者,心存一网打尽之计,具呈官产处,愿缴巨金归一手包认”,指责政府正是看中公司所缴纳的巨额款项,才给养鱼公司批准执照,同时也谴责养鱼公司试图将湖泊之利一网打尽,而不顾众人生计。
1930年代在湖荡资源丰富的地区,政府出租公共河湖已呈普遍之势,用出租大水面的收入兴办教育等公共事业,也一时成为风气。萧山县在1927年由党政联席会议议决,准备将县有各处鱼荡投票出租,其租金定案充作“教育经费”,并令各鱼户自次年起遵照规约向该会承租养鱼。同年江阴县在政府公告中也明确倡导“全邑支河,宜养鱼生利”,鼓励民间充分开发利用自然水面。江阴县政府保证,养鱼者如果遇到偷鱼毒鱼等事发生,官方将及时提供保护并出面制裁。至1934年,在河湖资源丰富的昆山县西北乡,已成立大规模的养鱼公司十几家,除利用“河道湛清、水草繁茂”的河流水面之外,还把充满天然饵料的阳澄湖边缘区域开辟为养鱼场。
在官河湖资源被用于商品鱼生产的风潮中,养鱼公司的逐利性使得他们不断谋求大面积的水面,并垄断水面的使用权,最初对于兼顾渔民捕捉野生鱼以及允许农民罱泥捞草、不妨碍农田水利的承诺,往往无从兑现,从而引发社会争端。
在不断发生的官河湖养鱼纠纷中,萧山白马湖养鱼事件具有典型性。1933年初,萧山县2500余亩的白马湖(包括东、西湖)由县政府包租给兴业养鱼社,该社虽在租赁协议中承诺将不妨碍渔民入湖,并将维持农民夹草罱泥的习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层筑箔簖,封锁湖面,不准渔民捕捉鱼虾,过往船只横加稽查,撑流竹木亦多阻碍”。结果在4月份就被渔民联合状告到县政府,控其“阻碍水流畅泄,非但有害十数村农田水利,仰且妨碍数千家渔民生计”,请求县政府撤销租约,拔除箔簖,永禁白马湖用于蓄养鱼类。其间公司方与渔民发生数次械斗,8月初还发生一起因渔家女入湖,被养鱼社管理人驱逐而溺湖身亡的事件 ,引起了社会公愤。最终在8月下旬,县政府不得不撤销与养鱼公司的合同,最终恢复了周边渔农民的传统生产习惯。
归纳起来,各地养鱼公司遭到民众抵制和投诉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公司方本能地垄断水面权,当初设想的兼顾周边民众生计的理想状态,在商业利益面前无法实现;二是影响了河流湖泊最基本的旱涝排蓄功能,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区域社会安全,洪涝灾害发生时矛盾尤为尖锐。因此对于涉及区域水利和社会安全的养鱼事件,政府的处理态度总体上是严厉的。例如1918年10月7日,浙西水利议事会决定废止嘉兴顶显荡、嘉善白龙荡、马呜庵漾等多处湖泊养鱼,其理由就是,各养鱼公司“所设之鱼断(簖),重帘密布,平时已足为河流之障,若遇上游盛涨,阻扼咽喉,势必酿成巨灾”。并规定在这些湖泊内,“旧有鱼簖尽行取缔,不准新添,亦不得移设他处”,如果遇到水灾年份,各县区职能部门必须“依照成例前往查勘”,以免私自养鱼重复发生。但政府方面的严肃管理,一般是针对重大事件,为平息民众怨愤,以免酿成更大事端,绝大多数未遭到投诉的养鱼公司,并非与公共水利没有矛盾,而是处于隐性的状态。
养鱼公司先占水面却不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也很常见,这使得官方难以有效地协调养鱼牟利与地方公共水利的关系,相关举措仅具事后补救的性质。1927年萧山县党政联席会议决议将县有各处鱼荡投票出租,其租金定案充作“教育经费”,但两年后的调查却显示,全县出租的鱼荡130余处之中,照约承租手续合格者仅有80余处,即使已承租者也大半拖延租金,按时交纳租金者寥寥无几,且有日趋减少之势。县政府担心长此以往公司养鱼“势将无形取消,则鱼棍顽强得计,公家威信扫地”。各地养鱼公司频遭投诉的现象也同样说明,政府对公司租用水面的水利关系评估和创办前审批手续方面的管理并不严格,否则便不用依靠事后补救来解决矛盾。
官河湖养鱼在民国时期持续发展,产量和经济效益究竟如何呢?由于缺少系统资料,以下分别从商办养鱼公司与乡村合作化形式的河道养鱼两个角度进行个案考察。
先看商办养鱼公司。养鱼公司所圈占的大型自然水面,原本以生长野生鱼和其他多种动植物水产为主,将其改造为以增殖鱼类为主的人工环境,必然对饵料结构、饵料投放量以及管理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养鱼者如何应对大型水面的水利功能由原来的区域综合性转向单一商业化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上,当时的技术和制度条件显然难以有效地提供支持。养鱼公司并不具备大量投入添加剂饲料的观念和实力,人工繁育廉价鱼苗的技术也尚未成功;而在政府一方,虽然看重自然水面养鱼的商业价值,却没有应对民生和水利矛盾的良好方案。
从笔者所阅读的民国时期有关农场化养鱼的史料中,并未发现鱼产丰收的案例,养鱼失败或收成不好的案例却比较常见。例如据1933年《工商半月刊》对昆山自然水面养鱼业的总结,该县规模最大的大盛养鱼公司,占有水面千余亩,但连年养殖并未获利,归纳其原因,“其养殖时之管理,未免不周,鱼种放入后,给饵量及时间均不一定,视采饵船来之迟速及多寡而定,故损失颇多”,可见管理技术不善和饵料供应链条不稳定都不适应大水面养鱼。而在上一年,该公司因一场洪水造成了鱼类逃散,赔本数万元。认为,昆山养鱼公司虽多有创办,但“唯因管理不易周密,失败者居多”,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因此应聘请农学专家帮助详密规划,并盼望低成本的人工鱼苗早日繁育成功。从具体数字来看,自然水面养鱼的产量偏低,至少是与投入的大面积水资源成本不成比例。镇江县永固、高资二乡利用自然水面一千多亩发展养鱼,结果根据1929年的统计,每年出鱼仅300余担,平均每亩产鱼不到30斤 ,这个数字仅仅相当于苏南浙西地区十几亩鱼塘的产量。
以上所述主要是公司化养鱼的管理和技术局限。这一产业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只依靠本地生态饵料和不改变水质的传统养殖技术,是否能够达到在广阔河湖中大规模养鱼以增产的目的?正如1947年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所总结的那样,在天然湖沼中养鱼,“如果能投入一些饵料或肥料更佳”。看来时人已经认识到,提高河湖养鱼产量的可行之路,是像池塘养鱼一样投放人工饲料、人工添加剂、给水体增肥等。但这样一来,就等于要将河流湖泊变成精养型的鱼塘,自然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水利功能均要发生根本改变。如果将圈占大水面引起的水利纠纷、旱涝灾害风险以及相关损失考虑进来,自然水面养鱼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了。
接着再对合作化形式的河道养鱼做一考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政府推动下兴起乡村合作化运动,太湖平原东部缺少大湖大荡的地区也开始推行自然河道养鱼,试图达到增产创收的目的,但若以产量对比所投入的环境与资源成本来衡量,成效同样不佳。
例如,1931年无锡县政府在高长岸村试行养鱼合作社,其首要问题是寻找适合养鱼的河道。最后选定村庄东面一条和外荡不通的河浜,但那条河浜周围都是稻田和茭白田,被土坝筑断作了鱼池后,船只便不能行进,影响农户运输肥料和农产品。在农民要求下,合作社给予他们赔偿补贴。后来工作组为了不影响船只通行,将土坝换成软竹篱,改用活水养鱼,但鱼的收获却失去保障。结果在1932年夏天,高长岸村利用活水养鱼遭到严重挫败。7月间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导致养鱼合作社破产,“建筑的堤岸和竹篱完全沉没,鱼逃跑了,农民们为了用机器把旁边稻田的水抽出来,就把竹篱拆开了一段,以便把机器船开进去,于是一部分未跑掉的鱼,也在那缺口处跑掉了”。最后在合作社的坚持下,活水养鱼在1933年冬天总算有所收获,10亩鱼塘收获鱼1000斤,平均每亩产鱼100斤,收入还不敷人力成本和鱼饵的投入。自此高长岸养鱼合作试验不了了之。
高长岸内河养鱼的模式、鱼产量的微薄以及遇到的水利矛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太湖平原东部和北部地区具有普遍性。嘉定、上海、宝山等县在政府的推动下都曾开展合作养鱼。农民在合作社的组织下,“利用本村河沼中之浮游生物、水草、螺蛳等类充作鱼类饲料”,划出一些小河小浜养鱼。但其结果与无锡高长岸相当一致,养殖面积从未铺开,农民积极性不高,最后都停留在试验阶段。1935年上海县塘湾村组织养鱼合作社,经过动员,农民仅集资50余股,筹得28亩水面,放养鱼种仅3000尾 ;1937年松江县9个养鱼合作社的养鱼水面经过两年筹备扩大后,也只有92亩。可见高乡地区的农田水利与扩张人工养鱼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明显,虽然政府热衷于推动和提倡,但较低的收益和较高的资源成本投入,还是影响了农民利用自然水面发展养鱼的热情。
总之,利用大型自然湖荡或者自然河流来养鱼,作为近代商品经济驱动下水资源被商品化的一种表现,在民国时期得到持续扩张,但实践表明人们付出的综合成本与经济收益并不匹配。作为公共水利资源的大型河湖,本身就不属于用来垄断牟利的商品性资源。如果坚持垄断式的商业经营,只有借助现代技术和管理体制的力量,通过强力改变自然水体的性质,并且为水利生态改变而引起的环境和社会矛盾问题准备好应对方案。
本文以民国社会和经济转型为历史背景,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太湖流域人工养鱼业的业态分布、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并对当时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条件下传统养鱼业所发生的变革进行考察,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一)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养殖鱼生产形态,首先是代表了工业化以前已经发展成熟的江南生态农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李伯重对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研究指出,16、17世纪生态农业在江南地区已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取得良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可以作为今日倡导的生态农业的先驱。他认为传统江南生态农业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通过改造田地,把不同的生产活动配置在水土条件最有利的地方,其二,是通过废物的再利用,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废物对环境的污染。鱼类养殖业作为江南传统生态农业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以上两个特点在人工养鱼业的主体——池塘养鱼业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池塘养鱼业分布在地势低洼的水乡平原,鱼塘改造更合理地利用了低洼地的水土条件,提高了生产率,大面积推广后,在苏南、浙西地区形成了稻、桑、鱼三业互相依存互为促进的格局,带动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同时,池塘养鱼在民国时期的产量和商品化程度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所有的淡水鱼生产方式中最具有集约性,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需求。另外,池塘养鱼的饵料也可在区域环境框架内解决,充分利用农产品加工的下脚料和农业废料,而不需要外源性的能量投入。综合来看,这种养鱼模式符合生态农业发展的取向,对于应对人口增长和社会需求增长压力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借鉴意义,是值得维持和推广的。
(二)外荡养鱼因占用水面大,并且产量较低,就其市场供应能力而言,只是作为池塘养鱼的补充,但作为湖荡资源综合利用的形式之一,其生态经验也值得总结。外荡养鱼与种菱、捞草、积肥等农业用途共存一体,保持养殖鱼的品种和数量与农业对水资源的需求相平衡,是外荡利用中的关键。这种平衡地利用自然水资源的方式,在民国时期的江南水乡稳固而普遍地存在,虽然常有外荡养鱼户试图通过扩大水面和增加鱼苗投放来增产,但以利益共享为基础的水利维护机制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三)在当时发展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受益面最广的官河湖水利系统受到商品化和增产观念的挑战,开始成为人工养鱼业扩张的主要场地。人们不以自然河湖出产大量野生鱼为满足,试图将其变为养鱼农场,但其低微的产量却与付出的水环境代价和引起的社会矛盾不相匹配。然而当时社会对官河湖水资源利用的商业动机是明显的,探索如何使其增加水产的行动始终没有停止。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营养鱼场的强势扩张,围湖养鱼一时成为风潮,原来已露出端倪的水环境问题集中爆发。一些地区围占大片湖泊改为鱼池,大量投入肥料和鱼苗,但事先却未开挖泄洪通道,不仅打乱了水系,出现洪涝灾害,且使得沿湖社队的积肥运肥、交通、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等都出了问题,官河湖大量出产野生鱼的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本文对民国时期官河湖利用观念裂变的考察来看,民国时期养鱼观念和方式的商品化及其环境效应,只是工业化时代人地关系变革在其前期阶段的一种反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