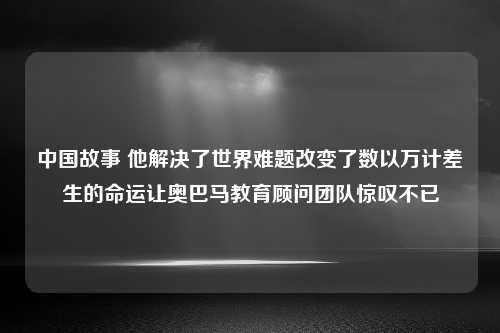85部全世界最好的小说开头堪称神来之笔!
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霜打磨,依然散发思想和艺术的魅力。而不少文学名著中开头,往往是整部著作的神韵所在。它们或将人深深吸引,或令人陷入深思,使读者欲罢不能。一起来看看,文学作品中,那些最经典的开头。
开头: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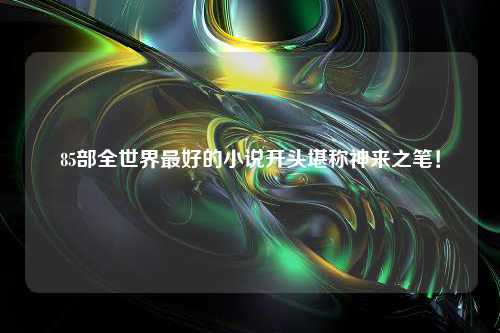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吉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势较高、种植小麦的平原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
我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
事后才有人想起来,1950年公历10月24日,旧历九月二十四日那天恰好是‘霜降’。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她记忆中的冬天,雪是大地唯一的盛装。天寒地冻之中,散落在雪原上的黑帐篷是避难之地。煮茶的残火在昏暗的空间内闪烁微光,浓香气味随之蜿蜒弥漫开来,带来由食物所构成的最朴素的诱惑,和最原始的抚慰。外面是迷境一般的寒冷,黑帐篷的毡片因为雪积三尺而无法拉开。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拔出来,打球了。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那天,比利・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的阿伯罗温下了矿井。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尺山的峰峦后面。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
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然后,她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1801年。我刚刚拜访过我的房东回来——就是那个将要给我惹麻烦的孤独的邻居。
多年之后,面对行邢队,奥利雷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
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但除了那个卑鄙的凶手之外,没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领事正襟危坐在自己的乌木阳台之上弹奏着那架历久弥新的斯坦威钢琴,用升c小调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序曲》;与此同时,巨大的绿色蜥蜴在下方的泥沼之中蜿蜒逶迤。
她的眼睛已瞎了多年,眼珠塌陷,人们却在其中看到十分锐利的光芒;她那干裂的嘴唇永远都是苍白的,不知多久没有人吻过;不穿鞋子,她素来赤脚走路。因为曾从血泊中趟过,她的脚底是红的,永不褪去的鲜红色,雨水冲刷后愈加明艳;她的长发,如蓄养的动物一般,一直默默伴随着她,一天天,由乌黑转为花白,还在不断地长,不断地长,像根须一样深深地植入大地,每次死神想要将她带走的时候,发丝总是纠结缠绕,绊住她的脚。死神只好放开她,让她多活了十年。十年又十年……
开头:每一个现在活着的人,身后都站着三十个鬼,因为自有人类以来,死去的人恰好是在世的人的三十倍。自从洪荒初开,大约已有一千亿人出没在地球这颗行星上。这个数字之所以值得玩味,只是因为出于奇怪的偶合,在我们这个宇宙——即银河系——也恰好有大约一千亿颗恒星。所以在这个宇宙里,每一个生存过的人,都相应有一颗星星在天空闪耀。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六0年一月,出生在底特律的一个丝毫没有烟雾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女婴儿;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
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那为什么会产生饥饿感?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为什么会缺乏食物?是因为没有等价交换物。那么我们为何没有等价交换物呢?恐怕是由于我们想象力不足。不,说不定饥饿感就直接来源于想象力不足。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拥有你那些优越条件。”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既然我还没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不会这样想了。
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个公共大厅里,一个男子向我走来,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曾经爱过你,那时你还很年轻,但与那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饱经风霜的容颜。”
洛丽塔,我生命之光,我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一丽一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一丽一塔。
我整个灵魂都充满了奇妙的欢快,犹如我以整个心身欣赏的甜美的春晨。我独自一人,在这专为像我那样的人所创造的地方领受着生活的欢欣。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挚友,我完全沉浸在宁静生活的感受之中,以至于把自己的艺术也搁置在一边。
我爱的花儿在高原,她的美很少有人看见;我爱的人儿在高原,他的笑容没有被污染。
我第一次看见特里·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上。
开头: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本书现在的作者保证读者诸君读罢本书后绝不会招来杀身之祸,而此种不幸命运曾于1691年《哈扎尔辞典》初版面世后,降在当时的读者身上。
我在这里要讲的事,别人本来可以写成一本书,然而,这段经历使我心力交瘁,使我的品德耗损殆尽。我只能将往事简简单单地写下来,它有时可能显得支离破碎,但我不打算虚构任何情节来弥补和撮合,我盼望这番叙述能带给我最后的乐趣,而矫揉造作只能破坏它。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